
本人擔任調解委員已將近20年,在這段期間裡因為調解處理過各種案件,也遇過形形色色的當事人,並要求自己秉持公正、客觀的態度進行調解,但公所的調解並不是法院,在調解案件時遇到更多的是情、理大於法的情況,而調解成敗最重要關鍵是取決於當事人的「態度」,因此有件案件至今令我印象深刻。
本案當事人之一阿玲,家境清寒收入不穩定,經濟來源僅靠擺攤維生,某日徒步穿越馬路時,遭到未成年小鄭所駕駛的汽車撞傷,但他卻未協助阿玲送醫並等警察到場就駕車離開。雖然阿玲傷勢不重,但也不得不暫停營業幾天休病養傷,工作損失及醫療費用更讓阿玲本不富裕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
我收到這件案件時,調解秘書有提醒我肇事者是未成年無照駕駛,調解時需多加留意。一進到調解室,兩造當事人皆已就坐,阿玲由一位友人陪同參與調解,而對造小鄭並未出現,是由身為法定代理人的母親出席,並委任律師陪同調解。說實話,在看到律師當下,內心其實有些不安,因為在以往的調解經驗中,當事人如委任律師陪同參與協調,多數會以「法律」的層面切入,常常會造成他造當事人產生心理壓力,甚至是引起爭執。
好在小鄭的母親所委任的律師並沒有強勢主導調解內容,對於這個案件的肇事責任也沒有過多的置喙,只希望阿玲能提出醫療單據及相關損失證明等文件。而阿玲這邊或許是沒遇過這種狀況,且當下過於緊張,僅口述車禍後所造成的傷勢及帶來的影響,無法提出相關醫療單據及資料佐證。調解到此,我建議擇日再安排第二次調解,並請阿玲攜帶相關證明單據,畢竟如果僅憑口述就要他人賠償所受損失是有失公平性的。
第二次調解時,所參與的當事人和第一次一樣,這次阿玲僅帶了近期的收入單據及報稅證明,並聲稱醫療單據已經遺失了。而我依她先前的供述初步計算了大約損失的金額,約莫是數萬元左右,但阿玲提出求償的金額卻是十餘萬元。此時我頓感為難,委婉詢問小鄭母親的意見,她表示:車禍初判表上所載小鄭有肇事原因,又未成年無照駕駛且肇事逃逸,至於阿玲因為家境清寒,車禍帶來的不便確實對她的家庭造成一定程度影響。
小鄭的母親聽後可能是出於同情阿玲的處境及保護小鄭的立場,與律師討論片刻後願意以15萬元作為賠償,本件就此達成和解。
事後我重新審視這個案件,能夠調解成立確實讓我有些意外,更具體地來說是小鄭的母親善意的態度讓我倍感意外。因為阿玲所提出的單據與賠償請求的數額確實有所差距(甚至可以說是差很多)。
我明白在處理車禍案件中並不是誰弱勢,誰就有理!賠償的責任及依據還需慎重檢視肇生事故的起因及是否提供充足的損失證明等才能作為賠償的基礎。我同情阿玲的家庭背景及遭遇,但這絕對不是作為賠償的因素之一,所以委婉的向小鄭的母親說明阿玲情況外,同時也向阿玲說明她確實欠缺部分損失證明的依據,並希望她對於求償金額可以稍加調降……沒想到未等阿玲的回應,小鄭的母親便欣然的表示同意阿玲的請求。
我除了擔任調解委員外,同時也身兼寺廟的董事長,長期為神明服務及關心地方弱勢,在潛移默化下影響了我對調解案件的處理態度,在我經手的案件裡,我希望過程中除了符合公平、正義外,也能兼顧人道關懷。民眾聲請調解的原因無非就是想盡快排除糾紛,但調解會不是法院,能夠調解成立最重要的因素就是雙方皆同意和解的條件。
我想盡我的能力在調解過程中喚起當事人心中的善念,然後能夠大事化小,圓滿處理糾紛,也透過調解的機制讓雙方可以利用溝通得到彼此都能接受的最大公約數,而這個案件便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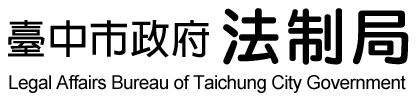
 Facebook
Facebook
 Twitter
Twitter
 LINE
LINE
